



美国第一位来华宣教士,为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会(美部会)所差派。先后在广州、澳门、上海从事文字宣教达3 0年之久。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份英文期刊《中国丛报》;参与翻译中文圣经,并先后参与创立了中国益智会、马礼逊教育协会、中国医药传道会,以及上海裨文女校等。他也可说是美国第一位“中国问题专家”。
1801年4月22日,裨治文出生于美国麻萨诸塞州的贝勒彻尔镇(Belchertown) 一个农民家庭,其父母皆为美国公理会教会的信徒。由 于家境贫寒,裨治文课余时间还要帮助父亲耕种田地。13岁时,在一次布道大会上,裨治文悔改归主。不久进入安赫斯特学院(Amherst College)读书。在学期间,他有机会阅读到一些关于海外宣教的杂志,使他对海外宣教有了初步的了解,遂萌发出献身作宣教士的念头。
1826年,裨治文进入安多弗神学院 (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) 深造。神学毕业后,于1829年9月,他成为美国公理会海 外传道会(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)的宣教士,接受差遣前往中国宣教。同年10月6日,裨治文被按立为牧师。面对那不可知的宣教工场的挑战,裨治文所属教会的牧师寇曼 (Lyman Coleman) 鼓励他要“ 高声地向成千上万已被偶像蒙蔽了心眼的中国人传福音,让他们得闻救恩的乐歌”。
促成美部会差派宣教士到中国的关键人物是英国宣教士马礼逊(Robert Morrison)和美国基督徒商人奥利芬(David W. C. Olyphant)。奥氏是一位信仰虔诚的基督徒,曾在梅森的纽约教会担任长老。1820年来华经商;1827年在广州成立自己的公司,名为“Olyphant & Company”。他与马礼逊关係密切,积极协助马礼逊在华宣教工作。1827年11月,马礼逊与奥利芬决定联手促成美国在华宣教事业,同时分别致函美部会请求建立中国传教团。奥利芬在信中具体要求派两名传教士来,分别向中国人及来华外国船只上的水手传福音。他们的请求得到肯定的回应,美部会派遣的裨治文与代表美国海员之友协会(American Seaman’s Friend Society)的雅裨理(David Abeel)于1829年10月14日搭乘“罗马号”(Roman)从纽约启程前往中国。在旅程中,裨治文记下这样一句话:“ 我虽然很渺小,但我的行 为将会影响许多人,甚至影响整个中国”。
经过三个多月的海上航行,裨治文等人于1830年1月22日抵达澳门,受到当时在华仅有的两位基督教宣教士马礼逊夫妇的热烈欢迎。那时,他们已在澳门和广州两地开荒工作了23年之久。这对初出茅庐的裨治文来说,实在是很大的鼓舞。
同年2月25日,裨治文转往广州。在美国租界内找到合适的房子居住后,即投入工作。他首先在马礼逊所创的一所小教会里做牧师,向租界内居住或工作的外国人传福音,同时开始学习中文。他视马礼逊为前辈,非常尊重他。在马礼逊的帮助和指导下,他度过学习中文、认识中国及适应生活的初期阶段。裨治文是一位富有远见的宣教士,他不仅有奉献的精神和事奉的热诚,更知道语言和文化对宣教工作之重要。他经常找机会与在租界内工作的中国人聊天,藉此操练中文会话。有时甚至冒着被捕的危险,向他们传讲福音。如是经过一年多时间,裨治文的中文有了显着的进步。除语言学习外,他还注重对中国文化、宗教及习俗之研究,为的是“将人的思想夺回,使它都顺服基督”(林后10:5)。
由于当时中国政府禁止其臣民与外国人来往,宣教士不得公开宣教,他们只得以文字和分发书刊的方式传播福音。奥利芬藉商务回国之机,发动纽约曼哈顿区布立克街长老教会的会众捐款,为裨治文购置一整套印刷设备交由美部会起运,于1831年12月运抵广州。1832年5月,裨治文在马礼逊和奥利芬的鼓励与支持下,创刊发行英文月刊《中国丛报》(The Chinese Repository)。目的是“ 唤起全世界基督徒对中国人灵魂觉醒之注意”。其读者主要是在中国工作的西方商人和宣教士,也供西方凡对中国有兴趣的人,以及在通商口岸能懂英文的中国商人和知识分子阅读。5月31日,创刊号问世。1832 年11月,美部会理事会秘书安德森(Rufus Anderson)赞扬说:“《中国丛报》是一份极有价值的刊物,办得非常好。我很高兴你决定让本刊进入第二年。它在美国传播关于中国的资讯并激发对你的宣教工作的兴趣,影响力很大,远超过我们期望之上”。
《中国丛报》的主要内容是介绍中国的社会、文化和地理等相关知 识,也记述宣教士们在东南亚各地如新加坡、马六甲、槟城、巴达维亚等城市的宣教活动。该杂志除报导中国语言、文化、历史、艺术、典制、风俗、宗教,以及迷信等内容外, 且屡次刊文针砭时弊,力陈妇女缠足,以及吸食鸦片之危害;以致废除妇女缠足成为西方宣教士努力的目标,并卓有成效。反对鸦片的文章,则前后刊载48篇之多,其中有15篇为裨治文自己所写,为中国仗义执言,并在美国激起反鸦片的浪潮。
《中国丛报》创刊于广州,在鸦片战争期间曾一度迁至澳门和香港,战后再迁回广州。裨治文一直担任《中国丛报》的主编,直到 1847 年他迁居上海从事译经工作时为止。其后,由宣教士贝雅各 (James G. Bridgman) 接任,但他只做了约九个月的时间便离职。从1848年10月起,美国宣教士卫三畏(Samuel Wells Williams)接任主编职务,直到1851年12月《中国丛报》停办为止。《中国丛报》从创刊至停办前后约20年,合共出版了20大卷。安德森于 1851年7月信中说:“我认为《中国丛报》是关于现在进展中的中国宣教事业半 世纪来最有价值的资料和意见的宝库。我切盼我们所有重要的图书馆都拥有整套的本刊”。
《中国丛报》不仅激发了西方教会和基督徒对中国的宣教热忱,更成为当时西方人探索与了解中国的重要媒介,在近代中外关係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在后世则成为学者们研究1851年以前基督教在华宣教活动的主要资料来源。 裨治文不仅是美国第一位来华宣教士,也是第一位汉学家。他具有热诚的奉献精神,特别的语言天赋,以及对文化的透视力。他用中英两种文字从事着述,向中、西方介绍彼此的历史、社会与文化,从而成为中西文化的桥梁。
1838年,裨治文出版了他的中文着作《英理哥合省国志略 ) (Brief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)。这不仅是一 本地理书,更介绍了美国的历史和制度,其用意在于显明美国文化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。此书前后经过两次修订: 第一次 在1846年,书名改为《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》,在广州出版;另一次则在1862 年,书名再次更名为《联邦志略》 (A Brief Accou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),在上海再版。
1841年,裨治文用英文写就《广东方言撮要》 (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),在澳门问世。此书详细描述了中国人在文艺、科技和生活等各方面情况。这部巨作面世当年,美国纽约大学 (University of New York) 为表彰裨治文在中、美文化交流上所作出的贡献,特授予他荣誉神学博士 (Doctor of Divinity)学位。
裨治文其他中文着述还有《真假两岐论》、《永福之道》、《复活要旨》、《灵生诠言》和《耶稣独为救主论》等书。此外,裨治文亦将中国的《孝经》翻译为英文。
1847年以后,裨治文移居上海,参与圣经的翻译工作,直到1861年在上海去世为止。他曾先后参与三部中文圣经的翻译工作,第一部 是《新遗诏书》,该译本基本上是从马礼逊的《神天圣书》修订而成的 。 1834年,在马礼逊逝世后不久,裨治文便开始与麦都思(Walter H. Medhurst )、郭实腊 (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) 和马儒汉 (John R. Morrison) 三人合作,着手进行马礼逊译本《神天圣书》的修订工作。1837年,名为《新遗诏书》的新约圣经在巴达维亚出版。
1843年8至9月,西方各基督教差会的代表在香港举行宣教士译经大会,商讨出版一部“不仅为各差会共同认可,亦为中国人所接受的圣经译本”。裨治文与波乃耶(Dyer Ball)二人,以美国公理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。大会决定对《新遗诏书》再次修订,并且重新翻译旧约。裨治文作为广州/香港传教区的翻译委员,被委派加入专责小组,与宣教士怜为仁 (William Dean)一起处理某些圣经专有名词的翻译。
1851年,裨治文与美国长老会 (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) 的宣教士克陛存 (Michael S. Culbertson) 合作,翻译旧约圣经,同时参与《委办译本》新约的修订工作。1859年,在美国圣经公会的资助下, 修订后的新约圣经正式出版。1863年,《裨治文/克陛存旧约译本》以四册本的方式面世。可惜的是,裨治文和克陛存都没能看到此译本的出版,因为他们已分别于1861年和1862年去世。
裨治文在其最后岁月里,还曾致力于将新约的历史书卷翻译为官话。可惜,该官话译本不知何故,未能传于后世,只能从其他宣教士的书信中,得知裨治文确曾从事这项译事。1861年12月,在裨治文逝世后不久,美国公理会宣教士白汉理 (Henry Blodget) 曾写信给他的差会说 :“裨治文博士最近写信给我,说他有六、七年的时间是常常忙于预备一部《四福音》和《使徒行传》的官话口语译本。我非常希望能够看到他所遗留下来的这部分圣经的手稿”。此外,美国宣教士丁韪良 (Willi am A. P. Martin)在其1864年7月30日写给美国圣经公会的信中,也曾提到裨治文的这部官话译本,是他与克陛存合作翻译的。
裨治文来华之初,在其头脑中,中国人只是一个“简单、落后和无知的拜偶像的民族”。但自从踏上中国的土地后,他所面对的异文化所带来的冲击,使他的世界观得以改变。他开始明白“ 这是一场对抗无知的现代化战争,决胜关键不仅是在于获得属灵的真理,也在于获得属世的知识”。同时他相信“ 教育是上帝用来提升人类心灵和解救人类脱离惩罚的一种方法”。这些观念上的改变,促使裨治文努力去协调中、西 文化之间的差异。
在裨治文和荷兰传道会 (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)宣教士郭实腊的推动与主导下, 1834年11月,一个为促进华人认识西方文化的组织“中国益智会”(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) 在广州正式成立。他们的目标是“希望藉着和平的手段,促使中国不论是在商业、西方文化或基督教信仰方面,全方位对外开放”。他们决意“以智慧作为炮火”,让中国人不仅可以接触到“现代的发现和发明所产生的最丰富的果实”,还可以认识西方国家的历史和国情。
中国益智会的主要工作是出版和推广中文书刊,藉此“开启华人的思想领域”。除裨治文外,郭实腊和马儒汉等宣教士,都有份参与撰写文稿的工作。美国商人奥利芬,英国商人麦雅各(James Matheson)和佐威廉(William Jardine)等人,都曾先后出任该会的会长 , 他们同时也是经济上最主要的支持者。在鸦片战争爆发前,中国益智会已出版了七种刊物,向中国读者详细介绍“那在中国以外、正在改变中的世界”。 后来,中国益智会亦在新加坡设立坚夏书院,出版中西书刊;同时承办郭实腊主编的杂志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》(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) 。
1835年1月,即马礼逊逝世后半年,裨治文和马礼逊的儿子马儒汉,以及一些在广州的欧、美商人,组成一个临时委员会,筹备成立 “马礼逊教育协会”(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) 和草拟章则等事宜,裨治文担任该临时委员会的召集人和书记。1836年9月28日,“马礼逊教育协会”正式成立,裨治文被选为理事会执行秘书。他在成立典礼上致词时说:为要完成马礼逊对中国教育事业的未竟之愿,该组织要在中国“兴办西式教育事业”,因为当“教育在中国普及化之后,全中国的人民将会受益,而我们的传教事业最终也会成功”。从中可见该会宗旨之一斑。
1839年11月4日,中国第一所西式学府“马礼逊纪念学校”(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School) 在澳门正式开学。第一期学生共有六人,皆为寄宿生。他们的学费、书费和食宿费等,均由马礼逊教育协会全额提供。校长为撒母耳·布朗 (Samuel Brown),他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,且在纽约已有多年执教经验。他的新婚妻子来华前也是一位教师,她愿意与丈夫同心负起领导学校之责。马礼逊纪念学校以英语授课的科目有地理、历史、算术、代数、几何、生物、化学、音乐和初级机械原理等,当然还设有圣经课程。该校学生虽因不习八股文章而不能参加科举考试,但他们毕业后可进入香港的洋行充当买办或译员。
1845年9月,马礼逊教育协会举行第七届年会,裨治文被选为会长。翌年,布朗校长藉陪伴妻子返回美国养病之机,带同容闳、黄宽和黄胜等三人前往美国麻萨诸塞州的芒松学校(Monson Academy)进修。其中除黄胜因水土不服,生病辍学回国外,容闳与黄宽两位均于两年后从芒松学校毕业。容闳继续前往耶鲁大学深造,而黄宽则前往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攻读医科。黄宽苦读七年后回国,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国外获得医学博士荣衔的西医。他先后在香港的伦敦会医院、广州的惠爱医院,以及博济医院服务,并于1867年担任博济医院代理院长。容闳毕业回国后致力于推动留美教育,“期盼政府能派遣留学生到美国读书,以便学成后能改造中国,振兴国运”。经过了十七年的努力,满清政府终于在1871年接纳了容闳的建议,派遣120名中国幼童,分二批到美国留学,容闳则被聘为留美学生监督。十九世纪后,容闳更成为了中国着名的改革家和教育家。
1847年6月,由于裨治文迁居上海从事译经工作,而马儒汉于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病故,再加上其他理事们皆私务缠身,因此在举行过第十届年会后,马礼逊教育协会便自动解散,而马礼逊纪念学校也从此停办。
裨治文携妻伊莉莎 (Eliza Jane Gillett Bridgman)移居上海第二年, 即创立“上海文学与科学会”,每月召集学人聚会交流,并印行学报。不久,该会更名为“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”(North -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),裨治文自任会长。
1850年4月,裨治文与夫人在上海创办了裨文女塾 ( Bridgman Memorial School for Girls),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学校,开中国女子教育之先河。“宋氏三姐妹”的母亲倪桂珍就是从该校毕业的。1881年,由于美国公理会与美国基督教女公会 (women'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of America) 之间发生分歧与冲突,裨文女校的部分师生转到美国圣公会所办的圣玛利亚女校 (St. Mary Girls’School) ,而裨文女校则被美国基督教女公会接管。1931年,该校以“裨文女子中学”之名向上海教育局注册立桉;1953年,中国政府予以接管,改名为“上海市第九女子中学”;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后,取消女中,再次更名为“上海市第九中学”。
1838年2月,裨治文联同美国公理会的医疗宣教士伯驾医生(Peter Parker) ,以及宣教士郭雷枢 (Thomas R. Colledge) 等人,在广州发起组织“中国医药传道会”(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)。该会成立的目的,旨在“ 呼吁欧美各国差会派遣更多医生来华,藉行医和开设医院推广福音工作”。当时参加成立典礼的有十多人,裨治文被公推为副主席。该会在联系早期医疗宣教士方面,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雒魏林(William Lockhart)、合信(Benjamin Hobson)和麦嘉缔(D. B. McCaetee)等在中国教会史和医学史上重要的医疗宣教士,都曾经是中国医药传道会的成员。
广州履任钦差大臣,颁令外商禁止贩卖鸦片。他是清廷少数有见识的官员之一,为要瞭解西方的政治、法律、经济、历史和风俗等情况,林则徐特意聘用了四位华人为他翻译外国书刊,并为他作传译,其中一位就是梁发的儿子梁进德。通过阅读,林则徐始知裨治文,并很想与他结交并使用他。由于梁进德是裨治文的学生,所以林则徐曾派梁进德走访当时仍在澳门的裨治文,请他前往广州相叙,以及协助林则徐把一份照会交给当时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 (Charles Elliot),并请义律转呈英女皇,期盼英女皇禁止种植罂粟,使鸦片商人无法毒害中国人民。裨治文虽然婉拒了林则徐的这项要求,但这份照会的全文则一字不漏地登载于1839年5月的《中国丛报》。裨治文还在报上发表了一项声明说 : “我们要告发英国,因她带头从事鸦片贸易。这个号称是开明的、跟从基督的国家,竟给尚陷在黑暗中、信奉异教的中国种植和生产有害的东西,且以此(鸦片贸易)补充她的国库。这展示了最奇怪的道德颠倒。我们深信,这个以善行和信仰原则作为基础的基督教国家,将会为她自己所做的事情——相对地与她当有的责任和荣誉不符的事情——遭受长期的苦楚。(英国政府)在一个异教的政府面前行事如此没有原则,这只会使他们(中国人)在反抗基督徒时落入 不道德的试探中”。
1839年6月3日,林则徐下令将查获英商的鸦片,在虎门销毁。 裨治文是应邀前往现场观看销烟的西方人士之一。在林则徐呈送道光皇帝的奏折中,如此提及裨治文等人的出席 : “臣等钦遵谕旨,将夷船缴到烟土二万余箱,在粤销毁。… … 其远近民人来厂观看者,无不肃然怀畏。并有咪唎坚之夷商经(King)与别治文(即裨治文)、弁逊(Benson)等,携带眷口,由澳门乘坐三板向沙角守口之水师提标游击羊英科迁禀,求许入栅瞻视……”。裨治文也将林则徐在销烟现场所说的话,登录在《中国丛报》上,其中有云 :“凡经营正当之贸易与夹带鸦片之恶行确无牵涉之船只,应给予特别优待,不受任何连累。凡从事私售鸦片之船只,必严加查究,从重处罚,决不宽容。总而言之,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。善者不必挂虑,如常互市,必无阻挠。至于恶者,惟有及早离恶从善,不存痴想”。
此外,裨治文也不时在《中国丛报》上撰文支持林则徐的禁烟运动。而在裨治文的巨著《广东方言撮要》的第六章中,他更将林则徐颁布的禁烟令全文登载出来,可见他对林则徐的禁烟之举是积极支持的。
1844年7月5日,中美双方谈判,清廷方面的代表为耆英和潘仕成;美方代表是特使顾盛 (Caleb Cushing),而裨治文与卫三畏虽则担任顾盛的译员,参与条约的拟定与翻译工作,结果是“中美望厦条约”的签订。其中第十七条款规定,基督教可在五个开放口岸设立礼拜堂并传道。有论者认为该条款得以纳入此条约中,与裨治文等人在中国民间所作出的贡献,以及他们与满清官员之间的交情不无关係。由于耆英和潘仕成两人,以及潘仕成的父母家人,皆为美国医疗宣教士伯驾医生的病人,通过接触与交往,他们对西方宣教士很有好感。因此,当美方争取在中国的传教权益时,耆英和潘仕成并没有提出反对,而且在他们呈交道光皇帝的奏摺中,也没有提出强烈的反对理由。故有论者认为,这些与裨治文在早前支持清廷禁烟,与满清官员建立一定程度上的相互了解有间接的关系。
1852年2月3日,裨治文因病无法继续工作,所以在妻子伊莉莎的陪同下,乘搭“野鸽号”(Wild Pigeon)轮船离开中国,6月16日抵达纽约。这是他们在华工作三十年中,仅有的一次休假。在美国逗留期间,裨治文无法忘怀在中国的事业。因此,他只在自己的家乡住了短短四个月的时间,便于同年10月12日离开美国,于翌年的5月3日抵达上海。随即投入到译经、写作、学术及外交等工作。1854年5月,裨治文随美国驻华公使麦莲从上海进入太平天国辖区考察,回上海后发表《调查报告》,否定太平天国。
1861年9月,裨治文罹患痢疾,以致10月举行的皇家亚洲学会会议,他都不能出席。延至11月2日,终因不治而在上海家中逝世,终年 60岁。自其神学毕业应召来华,历时30年之久。他的突然离世,令人深感震惊。其挚友卫三畏从澳门写信给伊莉莎说:“当我细读你寄来的几封信,以及勃朗博士在裨治文博士逝世前数天对他的情况所作的描述时,那有关过去的种种回忆,都涌现在我的脑海中。裨治文与你,每一天都在我的心裡。他是我亲爱的朋友——为他的存在,我有很多感恩的理由。我也盼望有一天能够永远与他在一起享受上帝。……他那不屈不挠的坚忍和那恆久不变的爱心,时常鞭策着我,要我以他作为学习的榜样”。裨冶文逝世后,伊莉莎返回美国一段时间。1864年,伊莉莎在北京灯市口创办了贝满女校,以纪念亡夫裨治文。1945年时名为“私立贝满女子中学”。1950年代之后,该校先后更名为“五一女中”、“北京市第十二女子中学”;现为北京166中学。贝满女中为中国培育出许多英才,原卫生部部长李德全、作家谢冰心、原上海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等人,皆出自贝满女中。伊莉莎于1871年10月去世,享年66岁。
斯人去矣,但裨治文在世时为中国社会和人民所作出的贡献,为后人所记念。他不仅把基督福音之光带到中国,也以真理和科学启迪了中国社会。他一生正如其名,注重“治文”,不愧为沟通中西方文化的“搭桥人”(Bridge-Man)。
载自:《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》 http://www.bdcconline.net/zh-hans/stories/by-person/b/bi-zhiwen.php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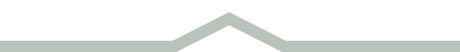
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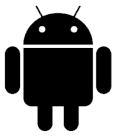
|

|